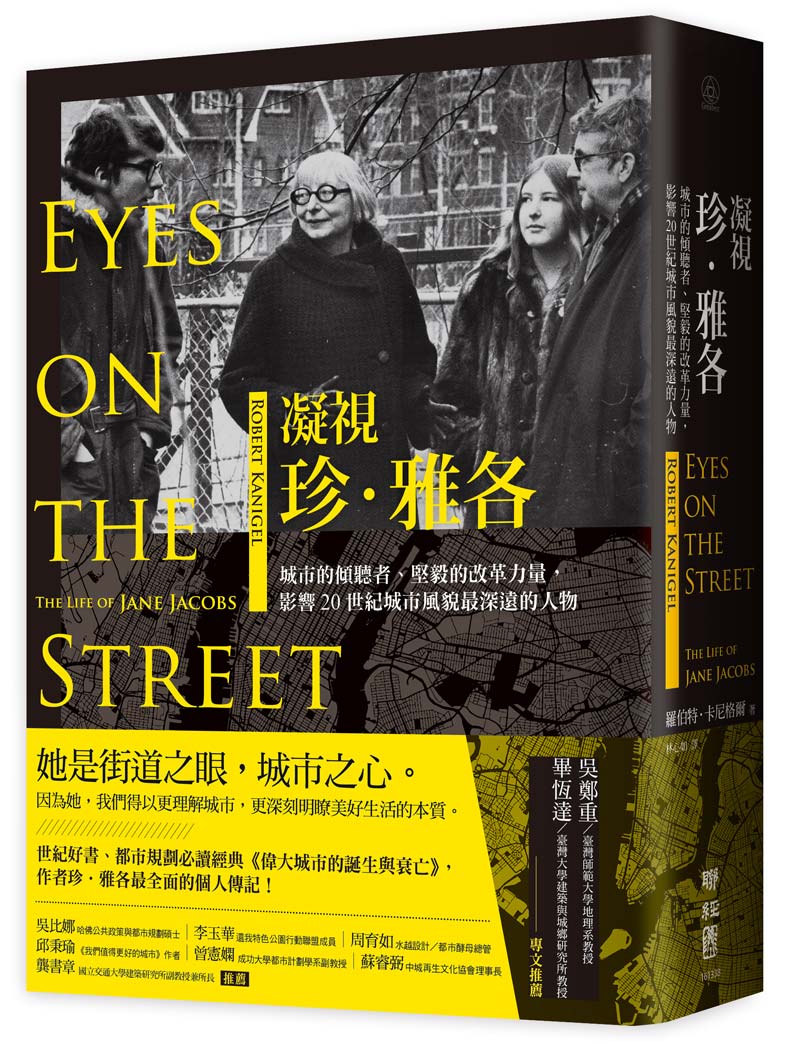位於紐約的林肯中心。圖片取自Flickr, Tim Ide, CC by 2.0
位於紐約的林肯中心。圖片取自Flickr, Tim Ide, CC by 2.0 懷特在一九九二年回想起他委託珍為《財星》撰寫、並將使她受到這般矚目和讚賞的文章時,記得自己當時判定珍「就是(做這件事的)那個人選」。雖說如此,〈市區是為人民而存在〉(Downtown Is for People)這篇文章其實原本會出現在世人面前的機率可說是微乎其微。
以懷特的說法,起初「她有所猶豫,並對我說她不打算寫;她從未寫過這麼長的文章」。懷特在《財星》的同事「覺得不應該」將這麼重要的一篇文章「發給她撰寫」,認為「她是女性,她的能力未受過考驗」。嚇,而且她通勤上班是騎一輛……腳踏車。總而言之,他們似乎覺得珍.雅各是「最不恰當的人選」,後來再也沒有談起她—根據懷特的說法,這讓珍鬆了口氣。但由於一個參與這項專題的資深編輯生病,珍的名字又浮上了檯面。而這一次,再無什麼能夠阻止她了。「她寫了又寫、寫了再寫,提出一份一萬四千字的初稿,而且認為編輯不會更動文章的任何一個字。我們的小綿羊變成了一頭母老虎。」
珍的作品掀起了軒然大波—不只是潛在地,而是就在當下、就在時代—生活公司裡。初稿在編輯之間傳閱時,懷特聽到「錯愕之至」的發行人傑克森要他們告知他這個「瘋女人」到底是誰?竟然在《財星》的篇幅裡提出要「支持並且平撫批評林肯中心(Lincoln Center)的人們」?那座大家殷切盼望、出色的新表演藝術複合據點的興建已經全盤就緒,且將使這座城市西區(West Side)的文化生活改觀。然而,珍卻將它描繪成一個有現代都市計畫所有錯誤的例子。

他們召開了一場午餐會議,與會者包括傑克森以及《財星》的編輯群,還有珍。「反對者起而攻之」,懷特回憶。傑克森質疑珍的報導有失準確;全名為查爾斯.道格拉斯.傑克森(Charles Douglas Jackson)這位先生是55歲的普林斯頓大學校友、戰略情報局(中央情報局CIA於戰爭時期的前身)前任員工、心理戰專家、艾森豪總統的講稿撰寫人、大都會歌劇院董事,以及林肯中心的長期擁護者。珍則以那是「事實和第一手觀察構成的長篇文章」來辯護。懷特始終低著頭;會議結束後,珍問他為什麼沒為她挺身而出。「我沒必要出場呀,」懷特答,「因為那個可憐人(指傑克森)已經踢到了塊鐵板。」
懷特的敘述前後不一致,可能有點太「加油添醋」,不像預期中那麼真確。他在一九九二年聲稱,初識雅各的時候,她在《建築論壇》的工作「主要是寫圖說」。這並非事實。她的確和其他員工一樣,也撰寫一本像《論壇》這樣照片豐富的雜誌需要的圖說,但這只是她工作最微不足道的部分;她五年前所寫長達好幾頁、經過大量研究的多篇文章代表了這本雜誌在城市議題方面的定論。而懷特藉由宣稱珍要求勿刪減她文章中的任何一個字,賦予她更貼近一個新進作家的地位,而非當時她身為的老練專業作家;珍比任何人都更明白一位編輯審校的重要性。
由於珍登在《財星》上的那篇文章直接導引她寫出《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因此懷特大有理由重新回望一九五七年的那些日子。回顧之下,珍當時即將邁向成功之途,而他—懷特就在那裡加以見證。但他在一九九二年究竟為什麼如此輕蔑地描述她,仍教人好奇。他和雅各夫婦是朋友。他們同樣熱切地讚頌都市生活、彼此敬重。也許是因為三十五年的時光已經使他的記憶模糊,又或許是將珍.雅各描繪成一個生手,會讓故事說起來更精采;也可能是他不知不覺地吸納了在《財星》的同事較多的偏見。也許,一九五七年的他純然所知有限。一如珍的兒子吉姆暗示的,懷特或許根本不知道,珍的作家和編輯事業當時已經長達二十年;「她不是那種自我吹捧的人。」

確實,這篇文章付梓的過程困難重重,懷特記憶中的這篇一萬四千字的初稿,被大刀闊斧刪掉了一半以上。儘管吉姆當年才九歲,也記得母親當時在寫這篇文章。「那真的很辛苦,她很擔心自己寫不好。」但是她確實做到了。而且伴隨這篇文章,她在哈佛演說之後逐漸開啟、朝向一個廣大世界的大門敞開了。
《財星》的系列文章從一九五七年秋天開始刊出。懷特在《爆炸的大都會》(The Exploding Metropolis)的導言中指出,這些文章十分傑出—它們後來被集結成書,畢竟它們是由「喜愛城市的人」寫的;在那個「郊區優勢」(Suburbia Ascendant)的年代,這樣的人僅是少數。七篇文章共同造就了山姆.巴斯.華納(Sam Bass Warner)為這本書再版中前言所謂的「一篇文化政治宣言」,試圖保有與過大的東西成對比的小規模和在地的事物。
懷特親自透過一篇標題聳動的文章,作為這個系列的導言—〈城市是否不適合美國?〉(Are Cities Un-American?),即使他並未真的提出、更沒有回答此一問題。之後,關於汽車和城市、貧民區、都市蔓延的文章逐月刊出;最後這篇再度由懷特執筆,他悲嘆「曾經綠意盎然的大片鄉間土地何以化為龐大、煙霧瀰漫的沙漠,它們不是城市、郊區,也不是鄉。
一九五八年四月,刊出了珍的作品。
大城市(她在開頭這麼寫著)準備好了要再興,新的都市再開發計畫正在進行。它們會是怎樣的呢?它們將寬敞如公園,不擁擠,標榜永續的綠意景致。它們將四平八穩又對稱,井然有序,乾淨、令人感到敬畏與不朽,具有一座妥善維護的莊嚴墓園所有特質。
她點名了好幾項這樣的計畫:舊金山的金門大橋、匹茲堡下丘區的複合展演廳、克里夫蘭的會議中心。它們不脫死氣沉沉:「這些計畫不會重新活化市區,反將使市區死寂。因為它們運作的目的恰與城市相互對立,排除了街道。」
珍的文章篇幅大約六千字,以雙倍行距的排版,占了大約二十五頁。文章觸及幅員廣大的地域、論及好幾座城市,同時搭配引人注目的配圖。實際上,珍用了頗大的《財星》昂貴房地產版面篇幅來談論城市街道。然而都市如果不是街道,那究竟是什麼?都市生活的嚴重缺失,豈不全都關係到不安全的街道,被交通阻塞的街道,醜陋骯髒而沉悶的街道?
或許是的,可是珍說,城市的任何指望都蘊含在生氣勃勃、豐富生趣的街道上;街道是體驗都市的地方。她帶著讀者,領他們停駐在舊金山的少女街(Maiden Lane),這是條面向單調市區樓房背後「狹窄、位於後門的小巷」。當地零售商用紅杉木做的長椅、植栽、藤蔓及窗臺花槽加以裝飾,營造出「令人無法抗拒的親密感、歡樂且自在不拘的一片綠洲」。市區所需要的—珍指出,是多樣性、對比還有繁忙,舊大樓和新的相互交錯、悅目的視覺焦點,像是阿爾靈頓街教堂(Arlington Street Church)尖頂突然出現在波士頓紐柏麗街(Newbury Street)上逛街的人視野中。這是從前城市可能且往往如此的狀態。那麼即將興建的新計畫呢?她喟嘆:它們屏棄了街道—以都市規劃師的新做法,街道再也無關緊要。如今,人們崇尚的是超大街廓,這些頂級的城市房地產區和舊街道拉開距離,後者遭到忽略。

東哈林區住宅計畫就分布在這樣的超大街廓中,斯特伊弗桑特城如此,林肯中心亦然。一番鳥瞰的景觀、一幅甚至以最粗略比例繪製的地圖,在在展現出這些巨大幾何形體中可能引起人們興趣的一切—龐大的現代派建築、集合公寓、購物中心以及對「文明」的謳歌;這一切都被倏然置入舊城市的緊密結構之中,龐大而乏味,用綠意加以點綴。
珍或者某個編輯為她的專文所下的一個段落標題是「大城市的『小』」。她寫道:「人們傾向於將大都市想成大企業,小鎮如小企業,這是大錯特錯。」相反地,應該在思考城市之際,朝小的方向思考。小型、各有專精、小本經營的生意—就像如今從東哈林區消失的店面「有賴它以外的供應商和技術」。它需要都市的廣大市場,也需要其他小本生意。新市區再開發的規劃並不考量任何事,而只在乎大—專門用於一個單一目的廣大同質性街廓。
比如引發珍和《財星》傑克森先生爭執的林肯中心,「這個大規模的文化街廓,」珍寫道,「預計將相當宏偉(此形容在珍筆下並非讚美),並且將作為紐約整個音樂和舞蹈界的焦點。」它即將在百老匯以西的西六十幾街被蓋起來,成為全國城市蔚然成風的那種文化複合據點。步驟一:凡是舊有之物,一律拆除。步驟二:在其間設立歌劇院、音樂廳或是藝術中心。但是,珍堅決主張,林肯中心和紐約的街景格格不入。周圍的城市肌理不會對它有所助益,它也不會對前者有所貢獻。不論它將為紐約帶來什麼樣的文化提升,都將從整體上使這座城市惡化。
珍的論點或許在那次跟傑克森、懷特午餐後軟化了,至少在它們化為紙上文字的版本中,她以近乎技術性的方式闡明林肯中心將如何漸次透過一條條街道和城市其他地方隔絕開來:「它北邊的街道上還會有一所龐大又陰森森的高中。南邊將是另一個超大街廓的機構,福特漢姆(Fordham)大學的一個校區。」然而珍談論的超出了林肯中心,更進一步論及超大街廓之運作如何損害城市。城市生活種種動力之間複雜而精微的交互作用,其街道視覺和社交的多樣性,其中人們、樓房及公園的多元,正屈服於一番死氣沉沉的新景象。而犧牲的是「令人想要來到城市並流連其中的歡樂喧嚷」,那正是我們正在失去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