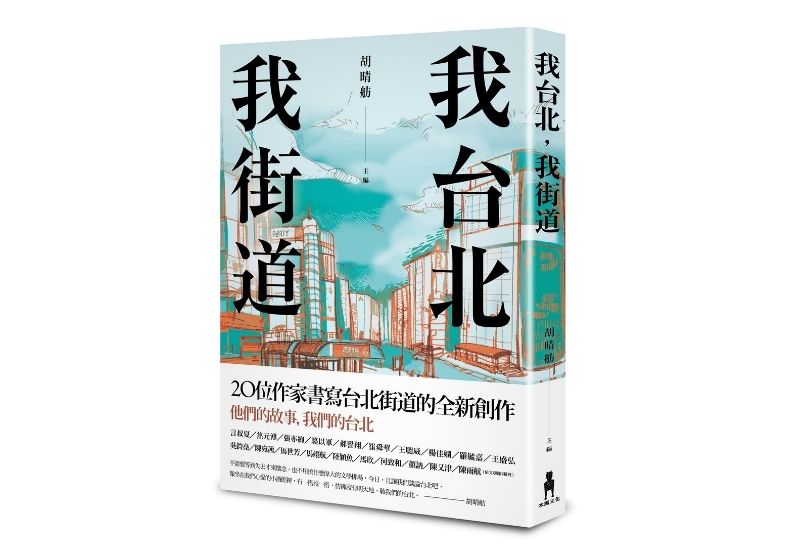Unsplash by Jisun Han。
Unsplash by Jisun Han。 若有一部時光機,我會來到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四日晚上十一點,安和路一段六十九號的「麥田」咖啡館。
這家店原訂十點打烊,卻總是不由自主開到深夜,時間愈晚,熟客愈多。你推開店門,人聲鼎沸,煙霧繚繞。「麥田」有一半空間是唱片行,播著羅大佑今天發行,剛剛到貨的新專輯《青春舞曲》。正放到B面第一首,激切迫人的〈盲聾〉。歌手在中華體育館舞台放聲嘶吼:
有人因為失去了生命而得到了不滅的永恆
有人為了生存而出賣了他們可貴的靈魂
心中深處的天平上你的慾望與真理在鬥爭
曾經一度自許聰明的你,是個迷惑的人
這是台灣破天荒的個人搖滾演唱會實況專輯,然而銷量不佳,因為羅大佑根本沒心情跑宣傳,他馬上要出國了。父親替他訂了三月九日飛紐約的機票,希望么兒遠離台北的是非,專心準備醫科考試。三十多歲的人了,老是不務正業,不是個辦法。
話說不太久之前,羅大佑的父親從高雄直奔台北,在「麥田」找到了他。老人一臉凜然,拿出移民表格,在咖啡店桌上盯著他簽了字。於是《青春舞曲》內頁有了這樣一段話:
「也許有少數人可以發現,我確實是演唱會中那個最孤獨的人……到了我告別一段時間的時候了,我總不能騙你說我腦袋裡還充滿著音符。多久?請別問我。」
你一眼就會看到坐在角落抽菸,滿腔心事的羅大佑,今晚還是不要打擾他。他不會知道,到了紐約認識一群藝術家之後,他將決心「棄醫從樂」。兩年後他會移居香港,做出震撼時代的《愛人同志》和《皇后大道東》。
看更多 》台鐵解憂藍皮列車出發!從屏東枋寮緩慢開到台東的懷舊祕境之旅
「麥田咖啡店」裡面這間唱片行的老闆,是音樂製作人李壽全—每個阿宅搖滾迷都夢想開一家唱片行,他替大家圓了這個夢。安和路這店面原本是台北最厲害的搖滾唱片行「木棉花」,一九八三年頂讓給二十九歲的李壽全接手經營,「木棉花」變成了「小西唱片行」—小西,是他新婚妻子的小名。
正好詹宏志打算開家咖啡館(這不就是文青的另一個大夢嗎),李壽全騰出一半店面,幾位好朋友湊錢認股,這才掛上了「麥田咖啡館」的招牌。「麥田」股東除了詹宏志、李壽全,還有羅大佑、「滾石唱片」總經理段鍾潭、副總經理吳正忠,和出版界的陳雨航、蘇拾平、陳正益、王克捷、陳栩椿—這十個名字,將會在接下來的二三十年,幹出許多轟動台灣文化圈的大事。比方一九九二年,陳雨航和蘇拾平一齊創辦的出版社,就叫「麥田」。
有個小青年滿臉笑容,蝦著腰推開門,肩上扛著個腳踏車輪,和認識的人一一招呼。大家哄笑:「『拿破輪』來了!」那不是二十六歲的李宗盛嗎。原來小李怕腳踏車被偷,索性卸下前輪,隨身攜帶,萬無一失。
座中笑得最大聲的,是一個義務役預官。小李指著他說:「張大春你別跑,張姊誇你寫得好,我他媽很吃醋啊!再寫個什麼來吧!」張大春說:「這樣,我又要回營,不定什麼時候寫好,到時候貼布告欄上,記得來拿,別人摘走了我可不管。」
一個半月之後,李宗盛嘔心瀝血製作的張艾嘉《忙與盲》上市,廣邀文壇健筆作詞加上概念式的組曲編排,轟動一時。他在唱片內頁寫下感言:「雖然我曾經參加過一些別的工作,但是我仍然醉心於唱片製作,並以自己能成為一個『製作人』為榮。同時我也很歡喜有很多朋友開始注意到『製作人』,並給予『製作人』應有的尊敬。」
你四處張望:角落一桌,是楊德昌和小野在談事情。你知道他們正在聊的劇本將會推倒重來,大幅改寫,在明年變成《恐怖份子》。隔壁桌是住在附近,客居台北的香港導演。他在香港拍的片子都變成票房毒藥,乾脆搬到台灣來另找機會。你很想偷聽他會不會和楊德昌交換什麼導演心法,但他正攤開紙筆為下一部電影做筆記,頭也不抬。這時候的吳宇森也不會知道,這部還沒開拍的《英雄本色》很快就會改寫他的生命,以及亞洲電影史。
看更多 》台劇《茶金》、捷運詩愛用!宜蘭專屬字「蘭陽明體」領先全台?
員工早就下班回家,只剩下二十九歲的「老闆」在吧檯後面煮咖啡、調酒、做蛋蜜汁,忙得不可開交。你知道,年輕的詹宏志還會愈來愈忙,漸漸沒空每天耗在店裡煮咖啡。再不多久,他就不得不把這家生意鼎盛的咖啡店頂讓出去了。
《青春舞曲》放完,詹宏志出來宣布打烊,你準備動身前往下一站。
「木棉花」不是爽心悅目的地方,
但,生命中有些特質容易被鼓舞的,
容易熱血奔流的,有敏銳音感的,
唱片是這些令人敬佩的藝人的結晶,
這種特質令人感動不已……
P. S. 本月份俱樂部會員私有唱片為 "Sea Level" "Return to Forever" 兩片
一九七八年三月,「滾石唱片」前身的《滾石雜誌》廿八期,有一頁「木棉花」的廣告,當時店面還在羅斯福路四段五十五號。
廣告是一幀滿版黑白照:一對青年男女在海邊,浪花掩上來,天空灰撲撲都是雲。男子長髮蓋過後頸(當年這樣的頭髮長度已經會被警察抓進派出所剃頭),背對鏡頭面海而坐。女子穿連身泳裝,面對鏡頭走來,一臉燦笑,頭髮被吹得有點兒亂,遠方是斜斜的海平面。看不出是哪裡的海,不過總是一個要坐一大段客運車纔能抵達,能讓你暫時忘記台北盆地的地方。
看到這頁廣告,你就知道:唱片行不只是唱片行,也是讓糾結的青春心事沉澱、發酵的根據地。啊對了,那兩張「俱樂部會員私有唱片」,確是阿宅級樂迷極難入手的內行之選,可以想見「木棉花」品味之高妙,聆樂幅員之深廣。
我會回到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五日深夜,羅斯福路「木棉花」舊址。我打算悄悄躲在角落,聽二十七歲的胡德夫和二十二歲的楊祖珺就著剛拿到的譜,一面學一面彈,錄下編成二部合唱的〈美麗島〉。
他們這天帶著吉他和新抄好的曲譜來到離「稻草人」並不遠的「木棉花」,借用店裡的器材錄唱〈美麗島〉和〈少年中國〉。這天的錄音,便是這兩首歌存世最早的版本了。時間緊迫,〈美麗島〉吉他彈錯好幾個地方,也來不及重錄了。
他們還不知道〈美麗島〉將會成為何等重要的史詩經典。楊祖珺唱到第二遍「我們這裡有無窮的生命/水牛,稻米,香蕉,玉蘭花」,在「香蕉」這邊憋不住差點兒笑場。論場合,這委實不大合適:畢竟今天錄音,是為了隔天一早要在朋友的告別式上播放。他是歌曲原作者,卻還來不及自己錄下新歌,就意外溺水身亡。他們手上的譜,是朋友曾憲政在他房間抽屜找到凌亂手稿,連夜謄抄出來的。
那位早逝的朋友叫李雙澤,這天的錄音後來迭經轉錄,地下流傳,和他生前彈唱的demo 一起,變成一小撮人的啟蒙密碼。〈美麗島〉將在兩年後成為一本黨外雜誌的名字,並將為台灣戰後最最驚心動魄的政治抗爭事件提供大標題,成為光芒萬丈的歷史符號。
我想看看他們年輕的,尚未被風霜淹侵的面孔,聽聽他們猶然清越嘹亮,樸實無心機的歌聲。後來,不管是他們還是我們,再唱〈美麗島〉,已經不可能回到這時候無牽無掛的心情了。
時移事往,如今你上網就能聽到胡德夫和楊祖珺年輕的歌聲,屢屢彈錯的和弦,和最後那個差點兒沒憋住的笑場。
看更多 》臺北小上海的前世今生-榮町百貨世界
或許,我應該回到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二日晚上九點半,羅斯福路三段二五六號二樓的「稻草人音樂屋」。或許,我會在那邊遇到李雙澤。
我會在滿座客人之中尋找一位粗框眼鏡滿頭亂髮的胖子。他偶爾也會去「稻草人」表演,彈唱Bob Dylan 的歌和〈思想起〉、〈雨夜花〉。但若遇到他,我該說什麼呢?
是否該說:「我知道你很快要回僑居地菲律賓,五月才回台灣,你一回淡水,就會跟梁景峰、徐力中一起拚命寫歌,用卡式手提錄音機錄下一批demo。聽好了:九月十號,你最好不要到海邊。要是看到海裡有一個外國人掙扎求救,不要理他,他沒事的。不要以為你很會游泳!要是非救他不可,回不來的會是你自己。欸,你根本還來不及錄〈美麗島〉!太可惜了!」
李雙澤百分之百會認為我是監視他的特務,專程來警告他行為收斂一點,否則恐有殺身之禍。他會輕蔑而警惕地看我一眼,才起身離開。這個經常一時興起泳渡淡水河的傢伙,根本不會把我的警告放在心上。我大概只會壞了他今晚看表演的興致,這可是他最喜歡的歌手:七十歲的恆春老人陳達。
如果你聽過披頭,滾石或鮑布狄倫,而沒有聽過陳達,只能表示你心胸不夠開闊,生活不夠豐富……
一句話:你的搖滾精神是假的。
——「稻草人音樂屋」刊在《滾石》雜誌的廣告,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去年聖誕節開始,陳達從恆春來到「稻草人」駐唱。今天唱完,就要搭晚上十點半的觀光號火車回去了,這是他回鄉前最後一場表演。
老人就住在「稻草人」的音響室,不唱歌的時候,常常坐在店裡發呆,喝茶,聽店裡放的Leonard Cohen 和Bob Dylan。據說陳達聽了Dylan 的唱片,說:「這個人唸的袂䆀(buē-bái),內底有英文嘛有台語,我帶兩張轉去參考參考。」
把陳達和「搖滾精神」連在一起,不知是「稻草人」老闆向子龍想出來的,抑或是張照堂的主意?那頁廣告的照片,就是張照堂作品:陳達在恆春自家外面,穿汗衫坐在藤椅上彈月琴,蹙眉高唱,木板牆歪歪貼著斑駁的「福」字。廣告寫道:「他的歌,既不商業,也不流行,可是他的歌卻使人想起泥土,鄉愁與遠方……」。
我會在靠近舞台的那一桌,遇見三十歲的母親和三十四歲的父親。不識字的陳達走唱江湖,總是即興編詞,問問在場有些什麼人物,再一一唱進歌裡,合轍押韻,好言恭維,這是賣唱人討賞的看家功夫。那天他唱到了我爸:「姓馬先生喔,是一個文秀才啊喂……」惹得我爸媽大樂。
母親面前桌上擺著卡式錄音機,架著麥克風。陳達一路從「五孔小調」唱到「思想起」再轉「四季春」,連續唱了二十四段,正好錄滿錄音帶一整面。那捲錄音帶在母親抽屜放了三十年,才被我重新挖出來,成為存世僅有的陳達「稻草人」實況紀錄。
啊我多麼想親眼看看陳達。看他手指如何在兩條絃勾按撥彈,看他唱出幾世人悲歡離合的那張缺了牙的嘴,看他僅存的那一隻悲鬱蒼茫的眼。
我願意幫他買檳榔和米酒,聽他絮絮叨叨的抱怨。然後若是可以,我會望向他的獨眼,一字一句地說:「阿伯,汝轉去恆春,身體若無爽快,就莫一個人佇外口行路,一定愛細意,千萬莫乎車撞著,拜託拜託。」
老人大概很難記住這樣的叮嚀。他無妻無子孑然一身,晚年耳聾目盲,精神狀態愈來愈混亂。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一日,陳達被一輛屏東客運公車撞倒在地。楓港基督醫院不敢收治,省立恆春醫院也拒收,救護車再轉往屏東醫院,老人半途就斷了氣。再過四天,將是他七十五歲生日。
而我畢竟來不及把自己拋進那個時代,只能獨自咀嚼一切遲到的歡喜悲傷與嗟嘆。
翻開羅大佑一九八三年《未來的主人翁》專輯內頁,觸目便是這樣一段話:
該走的路還很長、很坎坷,這個世界仍然大得我們看不清楚我們最近的地平線。開闊我們的心胸視野吧!讓我們一起努力,讓後來的人更好走,否則,三十年風水再轉以後,我們可別再聽到我們曾經抬頭問的那一句話:「這一大段時間,你們到底在幹什麼?」
我們的時代,是否也將成為值得嚮往的起點?哪些名字和聲音會被牢記?哪些故事仍能催人流淚?
我終究沒有一部時光機,這得等未來的孩子告訴我們了。
1.陳達在「稻草人」彈唱的錄音,第一句便唱「下昏二三暗正轉啊」(二十三日傍晚的時候),陳達原訂從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開始在「稻草人」駐唱一整個月到一月二十四日。但據張照堂回憶,陳達唱不到二十天,就想回去了。唱詞「二十三日」若指農曆十一月,就是陽曆一月十二日,駐唱第十九天,也符合張照堂的紀錄。
2.多年來,關於一九七七年九月楊祖珺、胡德夫初次彈唱〈美麗島〉、〈少年中國〉的錄音地點,包括楊祖珺的回憶錄《玫瑰盛開》,都記載是「稻草人」,直到二○一七年楊祖珺拍攝《尋覓李雙澤》紀錄片,訪問當年聯繫錄音場地的老友,才確定錄音地點其實是「木棉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