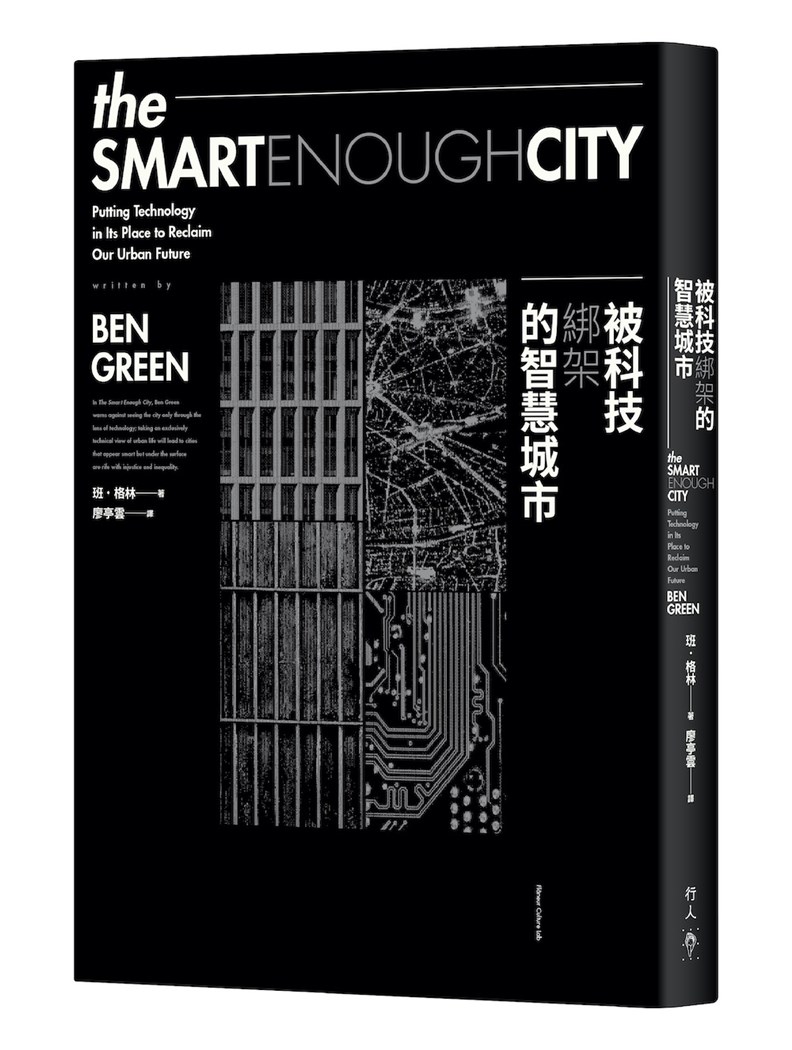科技狂熱者認定自駕車是通往「烏托邦社會」的路,但他們忽略了城市需求的多樣性。任何針對自駕車和交通的預測,一定都要先考量到誘發需求才能反映現實。
自駕車會提升行車速度和路上的汽車密度,當道路容量提升,行車需求也隨之上升,因為用路人會為了享有道路容量提升的益處,而更常開車。這種誘發的車流量會使壅塞變嚴重,尤其在尖峰時段,反而抵銷縮短行車時間帶來的益處。誘發需求的現象意味著,自駕車將進一步加劇美國普遍的都市擴張發展。
有個違反直覺的現象是,過去一世紀平均行車「速度」大幅提升;但平均行車「時間」還是不變,因為行車「距離」也提升了!

研究顯示,行車速度提升帶來的好處,並不是縮短通勤時間,而是移動到距市中心更遠的地方。這種隨自駕車而來的擴張,也會對環境造成毀滅性的後果:當人類居住的地點越遠,行車距離越長,汽車排放的溫室氣體也越多。
最關鍵的是,自駕車又犯下相同錯誤:把交通效率看得比適合行走和社區生命力還重要。
麻省理工學院的模擬,展示了沒有交通號誌的城市,汽車能以驚人的效率順暢行駛過十字路口。然而缺少了一項重要元素:人群。如果希望行人可以穿越馬路,就須向「自駕車不必減速地高速通過市中心十字路口」這種願景說不。就算設置紅燈讓行人過馬路,允許車子在街道上高速行駛,仍會導致城市變得更不安全、更不適合行走、也更沒有活力。
儘管提升行車效率有其價值,但並非城市唯一優先事項。如同上世紀付出的努力,是為了讓汽車更有效率地在街道行駛,促成了有利於汽車的都市設計。當試圖強化自駕車行車效率,也可能促成獨厚自駕車的都市設計,犧牲了行人、大眾運輸和公共空間。
把交通包裝成科技問題,也為私人企業提供了掩護。近年來,福特(Ford)宣稱自駕車會開創「交通阻塞大幅減少的未來」;Lyft 做出更大膽宣言,表示「終結塞車很簡單」,其共同創辦人約翰.季默(John Zimmer)指出:「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擁有了可以打造真正高效率交通網絡的工具。」

這把難解的塞車議題,粉飾成可用新科技輕鬆解決的問題,更誤導我們忽略其他方法。面對這類行銷說詞,有些政府考慮減少對運輸系統的投資,開始為自駕車公司鋪路。最大力鬆綁法規的州就是亞利桑那(Arizona),不少相關企業湧入首府鳳凰城(Phoenix),也導致2018年在坦佩(Tempe)發生史上第一件自駕車引起的行人死亡案件。
《適宜步行的城市》(Walkable City)作者傑夫.史佩克(Jeff Speck)厭惡試圖最佳化交通車流的做法,「我最不滿的就是,他們在進行市政論述時,抱持著霸權主宰心態。」
位於加拿大的多倫多,便採用積極探究、但很有原則的方式處理自駕車議題,示範了適宜智慧城市在面臨創新科技可能帶來的變革時,可如何妥善考量正確的問題和優先事項。
多倫多交通服務處長史蒂芬.伯克利意識到,城市必須主動追求理想的未來;而不是被動地讓科技主宰,然後祈禱有好結果。他把討論主題從原本的「汽車自動化可為多倫多帶來什麼?」修正為「如何針對自駕車制定計畫,又如何主導應用?」伯克利解釋:「我們不能讓科技反客為主!」

多倫多對於未來有明確願景,就是變得更平等、永續,且在經濟上持續發展。過去十年大力投資大眾運輸和步行環境,而不是開發新設施和為汽車擴增空間。「我們想減少交通阻塞,想鼓勵市民利用大眾運輸和動態交通(active transportation),想打造更宜居的城市,也想讓街道更有吸引力。」
他們分析了自駕車可能的所有權模式及其優缺點:私有、共享的隨需用途,儘管兩種模式在安全都具有優勢,但隨需自駕車較可能降低市中心停車需求、減少上路車輛數、為無法買車的市民提供交通選項。相較下,私有自駕車也許有助提升道路容量,但也會讓行車距離變長,導致更多空車佔用道路。
如此一來,無論自駕車是什麼模式,多倫多都可善用這項科技,並破解「智慧城市」和「愚笨城市」二元對立的錯誤假設。市府貫徹自身計畫和交通目標,同時善用科技帶來的機會。伯克利表示:「最好現在就採取行動,而不是放出瓶中精靈後,又得想辦法塞回去。」